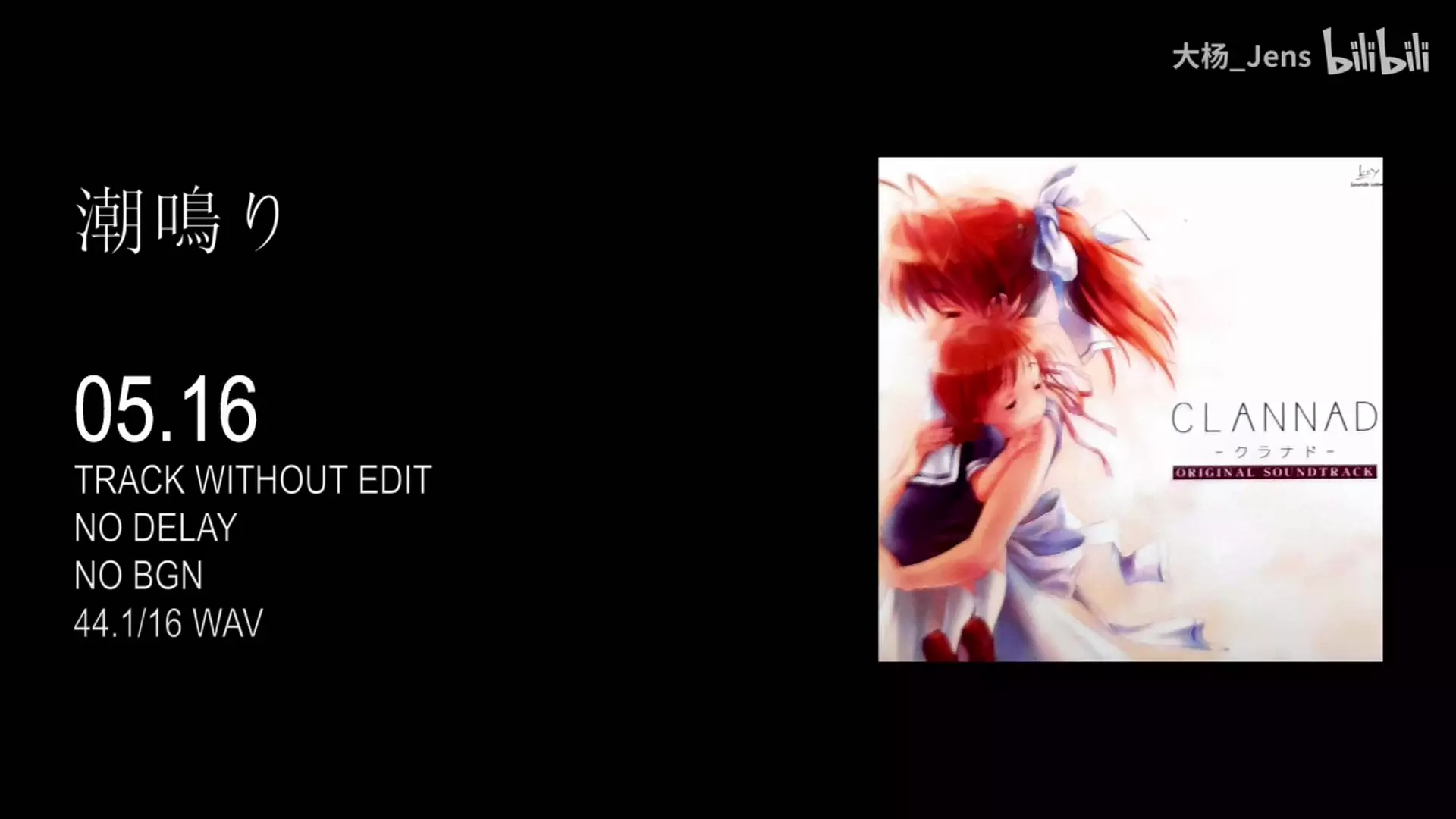青春的仓促告别 搬运uP主十六夜硝夜
初三那年的秋天,她转学去南方的前一晚,把一罐桂花糖塞进我书包,等你考上重点高中,我就回来找你,她站在站台的路灯下,围巾被风吹得猎猎作响,眼里的光比星星还亮,我们的异地恋从邮票和电话开始,她会在信里画南方的木棉花,说雨季里教室的墙会渗出水珠,我把月考的成绩单折成星星,在电话里数着还有多少天能在暑假见面,那时的距离像一根细细的线,我们攥着两端,以为只要用力就能拉的更紧,高一的暑假,她却说要补课不能回来,电话里她的声音很轻,带着我没听过的疲惫,是不是生我气了,我追问,她笑着说没有,只是南方的太阳太烈,把精力都晒没了,可从那以后,她回信的间隔越来越长,电话里的沉默越来越多,冬天的时候,她突然发来短信,我们分手吧,我冲到电话亭,打了十几个电话她都不接,最后接通时,她的声音冷得像冰,在这里有了新的朋友,我们早就不一样了,我握着听筒,听着那边传来的忙音,眼泪冻在睫毛上。那段日子,我把自己埋进书本里,像是只有这样才能抵消心里的空洞。直到高三毕业,整理旧物时,才在一封被遗忘的信里,翻出一张诊断单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,确诊日期正是那个夏天。信的最后,她写着:你该有明亮的未来,不该被我的黑暗困住。那一瞬间,许多细节一齐涌上来——她说过南方的桂花不香,电话里掩饰不住的咳嗽,笑声背后的迟疑。原来,她所谓的疏远,并不是不爱了。高中毕业后,我因缘际会去了南方。走过她曾在信里描绘的那所医院时,木棉花正盛开,枝头的火红映得天空发亮。花园的长椅上,一个熟悉的身影安静地翻着书,眉眼清瘦,却比记忆里更温柔。她挺过来了。经过了最艰难的岁月,病痛终于在一次次治疗中退去,青春被延续成了新的奇迹。那些年,她用最决绝的方式与我告别,只是为了让我不必背负黑暗。重逢的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青春里的仓促离别并不是终点,而是命运绕过千山万水后的重聚。后来,我们一起走过木棉花盛开的路口,像少年时那样并肩而行。她依旧是那个在秋风里递给我桂花糖的女孩,而这一次,她终于留在了我的未来。






 视频
视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