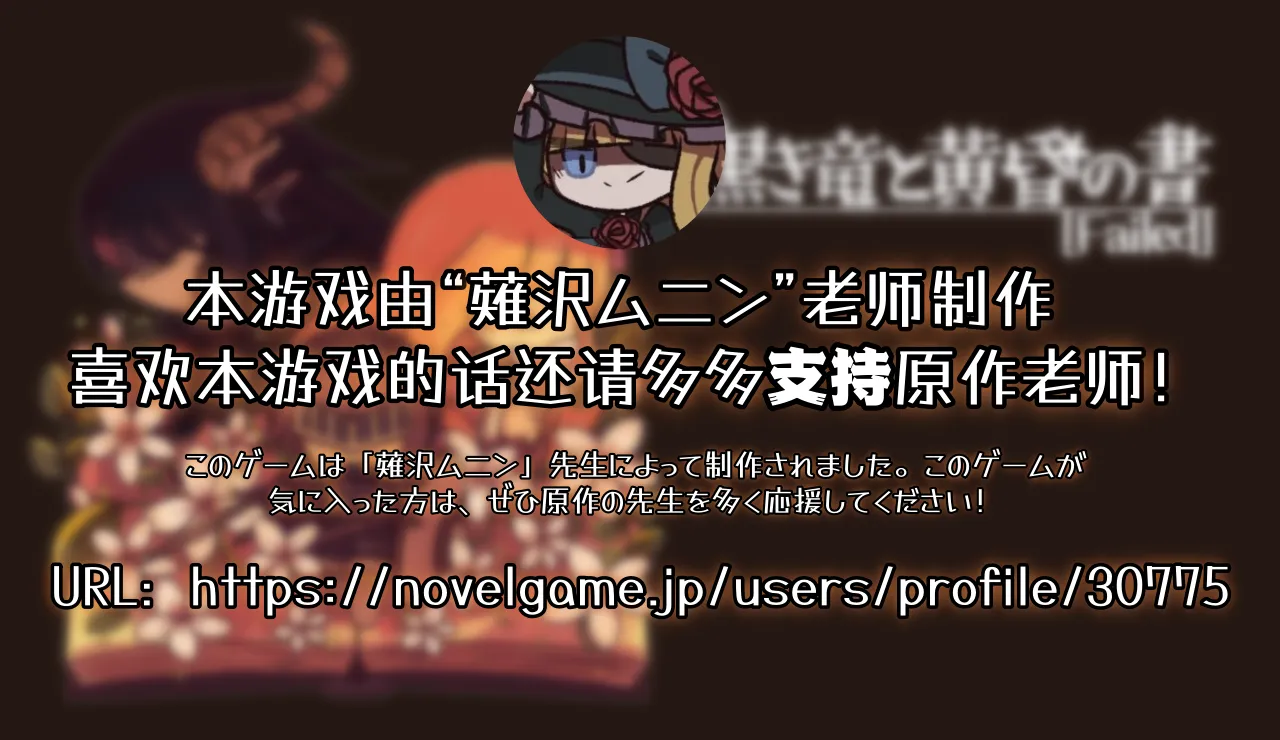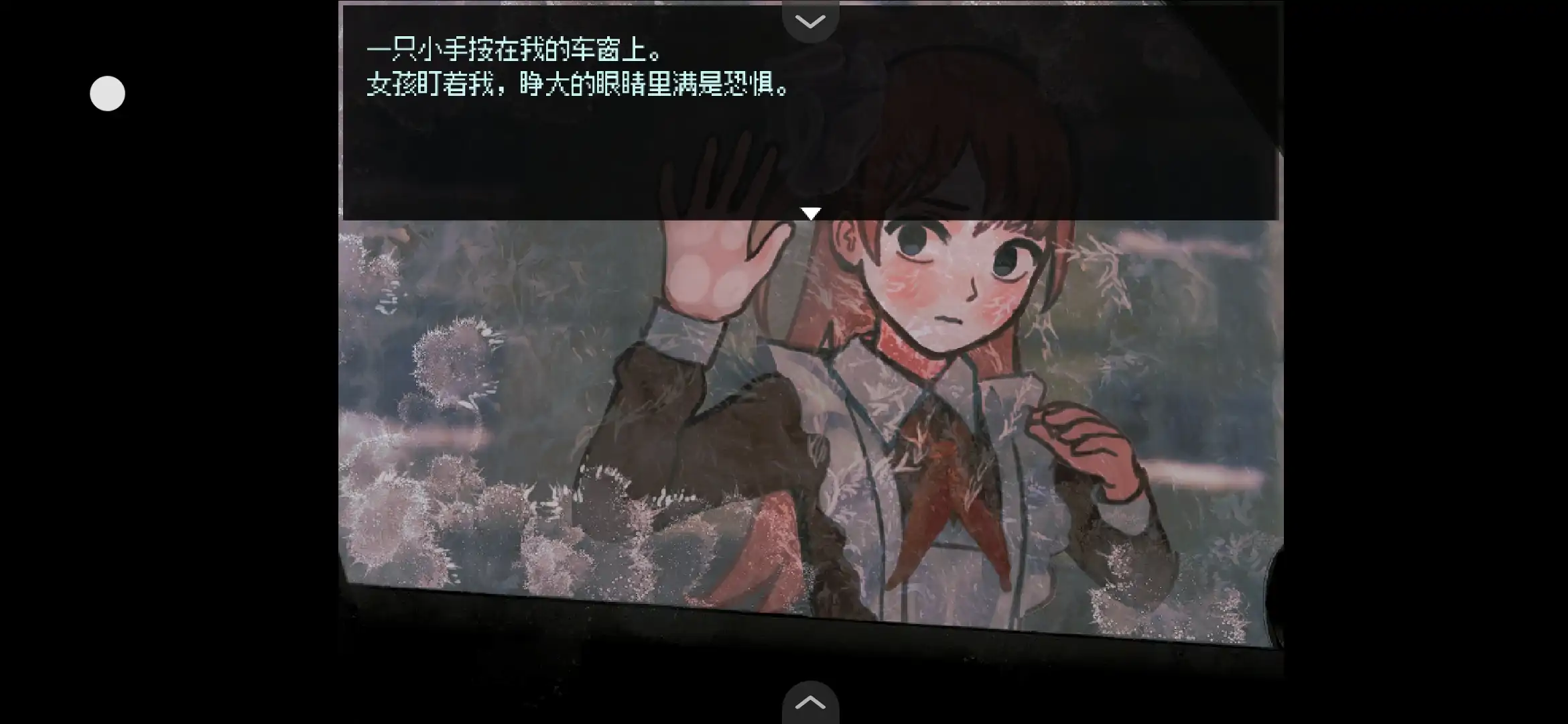
游戏衍生小说

io:这些故事是维奥莱特写的,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,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而且,多亏了她无尽的耐心与善意,她对我完成这个项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总之,我强烈建议你们读一读这些故事,另外,请到她的 AO3 主页去关注她吧。
三篇短篇小说:我会为你歌唱 & 一旦你走过,便再无归途 & 层层叠叠,如螺旋上升
~我会为你歌唱~
Lera 的香烟快见底了。这是个缓慢的过程。那些印着 “吸烟有益健康” 的早期苏联品牌香烟,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每盒新烟总会少几根,点燃时都散发着淡淡的、类似烧肉的焦味。这味道一次比一次刺鼻。
Nika 还没意识到这烟对她不好。她闻到烟味会皱鼻子,却从不反对。
她迷上了收集烟蒂。至于为什么,甚至从什么时候开始,Lera 想不明白,但她的烟灰缸总会变空。就连滴进空泳池里的烟灰,也会被什么东西扫走。
或许是 Nika。或许不是。
这里有更糟的东西,或者说,只是体积更大的东西。它就在她身后,却从不在她的影子里。她被它笼罩着,像大楼里的一只老鼠。“独处” 时,这种感觉最强烈。
Nika 打破了这份紧张,缓解了那份压迫。那股力量重得不可思议,仿佛她随时都会被拽回去。
Nika 把手放在她的手上,传来一阵阵忽强忽弱的热度,她才定下心来。可即便如此,要是盯着女孩的眼睛太久,偏执就会顺着脊椎爬上来。她已经有上百次确信,Nika 会把她推下悬崖。
可那是哪道悬崖,又为什么要推,她还是想不明白。
把未知当作常态,似乎也没那么糟。她绕着走的那个无底深渊,维度在变,引力时强时弱,至少还违背逻辑。在旧世界里,有某种无处不在的行为准则。人们期待她表现完美,随时适应新情况。上千条规则,只有她弄不懂。
她的核心是一种沉闷的灰色恐惧,这比这个地方更说得通。她的血在血管里,受科学约束。她遵从物理和生物规律。至少现在,她是可定义的,在某种程度上。
Nika 是一堆事实的集合。Luka 配合她的问答游戏,探索着彼此的定义。
Nika 最喜欢的东西清单很短:巧克力、蓝色、夏天(或者说这里能算得上夏天的日子)、狗、鸡、午后、肉糕、“多汁” 这个词在嘴里的触感。
这一切背后藏着什么。从背后看,她会变得陌生,变得不可知。问太多问题,就会有什么出问题。她不会再是个女孩,而是变成一只饥饿的矮脚兽,一团血肉,一枚扔进井里却永远落不到底的硬币。
好在,Lera 需要陪伴。她不能太害怕,毕竟 Nika 是她唯一的同伴。
这女孩不在乎 Lera 说错话。她会为 Lera 频繁发作的发烧和头痛操心,端来边缘掉漆的玻璃杯,里面是勉强算干净的水,还有罐装面包。要是 Lera 呼吸急促,喘得厉害,手抓着胸口,Nika 就会坐在她身边,笨手笨脚地读起章节书,想用故事安抚她唯一的朋友。
要是 Lera 说自己的坏话,说这栋楼的坏话,说这个世界的坏话,Nika 就会皱起鼻子。这种明显的不适,让 Lera 很少再说这些了。
Nika 也有糟糕的日子。不是那种若即若离、总出现在 Lera 眼角余光里的日子。不,是她生气的日子。什么都不对劲,她对着墙抱怨,用拳头砸泳池。挫败、无聊,还有挥之不去的不适感,最终占了上风。
这些日子里,她更像个孩子了。就算气得大哭、跺脚,也显得真实。仿佛她能从背上扯下什么东西,变回一个普通女孩。Lera 几乎最喜欢这样的她。
等 Nika 闹够了,她们就坐在泳池底。Lera 不会碰她,只会唱歌。唱着外面世界的歌,那些这里收音机里不会播放的俗气情歌。
这里的收音机里,只有战争广播、失真的古典乐,还有格外悦耳的静电噪音。
这些天,Lera 清晨缓过神来时,常会听见墙壁嗡嗡作响,发出呻吟。这声音越来越像音乐了。
~一旦走过,便再无归途~
在大学图书馆一个闷热的角落,Lera 找到了几本美国书。只有三本,封面单薄,译文生硬。亮面封面上的小美国国旗图案吸引了她的目光,手指抚过那图案时微微一顿。
一本政治学教材,一本 Norman Rockwell 的画册,一本心理学练习册。
只有练习册真正让她产生了兴趣。她随手翻开一页,实在太累了,没法从开头读起。
你会把自己当成婴儿抱住吗?
想象你自己或一个朋友。别想他们的不好。想象他们年幼时小小的、动来动去的样子。想象自己是个哭闹的婴儿,然后抱住 “他们”,紧紧抱在胸前。蜷起一根手指,勾住他们小小的手。
她的胸口突然一阵刺痛。巨大的铜铃在心脏空荡荡的腔室里回响。她能看见自己的未来 —— 刺眼的雪原,呛人的烟雾。图书馆里人工暖气明明很足,她却像冻伤了一样僵在原地。
她永远不会有那样一只可以去握的手,也永远不会有人来握她的手。她会孤独到时间尽头,像沙漠里的 Ozymandias(古埃及法老的化名)。只是这一次,她被困在钢铁与玻璃里,而非黄金铸就的雕像中。若胃里有东西,她恐怕会因这孤独吐出来。
那天,她彻底冻住了。未来的铁门随着铁链的嘎吱声缓缓关闭。
在公寓楼的深处,她能感觉到脚下的地板在搏动。瓷砖随着周围的 “mass” 一起收缩,连那片漆黑得纯粹的巨大虚空,也在同步起伏。
Nika 站在那里,一动不动,双臂张开。她笑得像头顶的星星一样亮。Lera 的心脏像被劈成两半,一半冷一半烫。她想念童年时的母亲 —— 那个在他们小公寓里如同仁慈神祇的母亲。她想在水管尖叫(指水管因水流冲击、管道老化或温度变化(如冬季结冰、热水流过)产生的尖锐声响(类似金属摩擦或气流呼啸的声音)。)时被人抱住,想有人用手轻轻抚过她的头发。她想回到自己还没变成母亲够不着的 “独立个体” 之前。
可她放不下。她听见最后一次通话时母亲的声音,像晶体管收音机里模糊的杂音,在脑海深处嗡嗡作响:
“好吧 Lera,他 —— 啊,抱歉,你知道我不擅长这个,她 ——”
当时每一秒都让她厌恶,可此刻她突然迈不开脚。痛归痛,她忘不了母亲努力的样子,忘不了如今节假日里两人笨拙相处的模样。
“Nika。” 这个词在她嘴里格外粗糙。她看见像虫子一样的筋腱从女孩的胳膊上爬出来,扭动着。她已经说了 76 次,失败了 76 次。
Lera 冲上前,伸手攥住 Nika 的手。温热的血肉贴着她的皮肤,她用力一拉,脚下的地板发出轰鸣。
“Lera,”Nika 几乎是尖叫,“放开我。”
“不。”
“求你了,融入进来会更好的。变成更伟大的存在,得到永恒的安宁。”Nika 说着,渐渐镇定下来。身后的墙壁发出尖叫与摩擦声,在她们身后重重关上。Lera 没理会,眼里只有前方的路,和手中温热的手。
她攥得更紧了。那只手也回攥过来。
~层层叠叠,如螺旋上升~
西伯利亚大铁路(Trans-Siberian Railway)将平原一分为二。金属碰撞声、机器持续的运转声中,火车正冲过荒原。它摇摇晃晃,怒吼着,一夜之间跨越千山万水。此刻,乘客们想必都蜷缩在铺位上睡着了。
Lera 浑身发冷,却在冒汗。她咬紧牙关,想着倒在雪地里该多轻松。经历了这么多,她依然渴望一场平静的死亡。死亡这习惯,太难改了。
若在这里失败,不会有寂静,不会有作为时间胶囊的躯体。她会变成一团红雾,一堆器官与血肉溅在钢铁上。冰不会保存她,不会让未来百万年后某个迷路的女儿发现她。
她疯狂地挥着一只手臂,另一只手紧紧攥着手电筒 —— 那是军队的遗物,光束直直照向火车的前窗。
没有躲闪的余地,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。Nika 裹着 Lera 的外套,在雪地里几乎一动不动。她胸口微弱地起伏,呼出几缕白气。两人的手指都冻成了深紫色。
汽笛尖锐地响起。Lera 没有动。某个部件卡进了位置,巨大的机械声对抗着惯性,发出呻吟。
摩擦声越来越响,最终变成尖叫,火花碎片散落在雪地上。
Lera 的母亲是在公寓里生下她的。刚一开始阵痛,她就喊着丈夫的名字 —— 他三个月前刚去世。邻居那位退休护士听到动静,过来查看情况。
分娩毁了那块地毯。16 个小时里,人体能分泌的所有液体都浸透了那块波斯针织地毯。没有药物,没有医生,没有医院。只有粗糙的手,和无尽的疼痛。
小时候,Lera 总在脑海里闪现那些画面。她只能凭着零碎的印象和想象,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场景。她把痛苦、鲜血、孤独和爱缝在了一起。
每个讲起这段往事的人都会笑。每一次笑声,都只会让 Lera 更愤怒。那是场悲剧,本可能夺走母亲的命。
这个念头钻进了她的梦里。在莫奈(Monet)的笔触下,她看见千种红色。她听见尖叫声,不知为何,她知道那是母亲的声音。时间一点点流逝,拖着她的痛苦。数字 16 总在脑海里盘旋,尽管她早上才会明白为什么。
她猛地惊醒,脑海里回荡着一滴眼泪落下的声音。她在被单里挣扎,哭得喘不过气。不知不觉中,一只手搭上了她的肩膀。就像在梦里一样,她知道那是母亲。这是本能,她永远能认出母亲。
母亲把她搂进怀里,紧紧贴着自己的胸口。母亲穿着白天的衣服就睡着了,布料蹭着女儿的皮肤。Lera 的睡衣洗得发白,是浅灰色的。
“嘘,” 母亲在暖气的嗡鸣中低语,“没事的,我在。”
Lera 埋在她肩头哭。慢慢的,她抽噎着平静下来,呼吸带着水汽。她想说的话堵在喉咙里,像爪子在挠。
“我出生时,你开心吗?我知道很痛。” 话说出来,她总觉得不对,可又想不出更好的表达。母亲把她搂得更紧,仿佛要把两人压成一个人。
“当然开心。” 声音很轻,却很坚定。哪怕再大声些,这话语里的力量也不会减弱分毫。
“一直都开心,” 母亲又说,语气稍缓,“你是我宝贝的孩子。他们对我做什么都好,为了你,都值得。”
Lera 回抱住她,浑身发抖,努力去相信这句话。
Nika 什么都想试试。Lera 力所能及地满足她,用最后一点积蓄买吃的、玩的,买火车票。她不知道钱花光了怎么办,也不知道火车最终到了太平洋边该怎么办。
Nika 到目前为止什么都喜欢:黏得像焦油的巧克力,刚出炉的面包,咸鱼。
她细细品味每样东西。她不急不躁,把包装翻来覆去地看,手指划过上面的图案。满意了,就像用开信刀一样精准地拆开包装。然后,若是能掰开,就掰一块放进嘴里,闭上眼睛。
她认真对待每一份自由的滋味,脸上写满了享受。
Lera 自己吃饭总是浅尝辄止,白天很少吃零食。她比以前吃得多了,可还是不够。她饿,冷,虚弱。她活得像只鸟,或者说,像个囚徒。
至少 Nika 吃得像个正在长身体的女孩。她总饿,连最难吃的东西也会盯着看。只要是新的、不一样的,她就满足。
可问题是,Nika 还在变瘦。不管嚼多少焦糖,有条不紊地吃掉多少司康饼,她还是饿。
无论她看起来多像人类,摸起来多温暖,她都不是人类。或许她有 14 个胃,永远填不饱。或许她皮肤下只有上等排骨。不管她是什么,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
她可能到不了符拉迪沃斯托克(Vladivostok)。
列车员让她们上了车,没收钱。乘务员跑到车厢后部取毯子,回来时怀里堆了六条。她的高跟鞋嗒嗒响,透着一股急切的善意。
“这边请,” 票务员被她们打断,有些慌乱,拿起一条毯子披在 Nika 肩上。女孩还没醒,但有呼吸了,体温正一点点回升,“卧铺车厢有张空床。”
Lera 冻僵的手指笨拙地抓起一条毯子,裹紧自己,浑身一颤。她想把 Nika 抱在怀里,却还是顺从地让票务员抱起女孩。剩下的毯子都塞到了 Lera 怀里。她跟着穿过拥挤的卧铺车厢,满是鼾声和沉重的呼吸。
这既让人安心,又让人难以承受。车厢尽头,门旁边,她们找到了今晚的床。Nika 先被放上去,盖好毯子,Lera 随后躺了进去。
她轻声说 “谢谢”,向票务员道别。
她专注地听着 Nika 微弱的呼吸声,伸手搭上女孩的肩膀。拇指画着圈,慢慢用力,想把暖意推回去。
或许 Nika 没有血管动脉。这轻柔的按摩可能毫无用处。想到这里,Lera 差点发出一声粗哑的笑。过去几天的恐惧还像锯齿一样卡在喉咙里。可她没停下,继续试着把暖意送回去。
当 Lera 用碎掉的汽水瓶割开缠住 Nika 的东西时,传来一声湿乎乎的撕裂声。血喷在她们身上,温热粘稠。这会毁了她们的衣服,已经浸湿了 Lera 的头发。
Lera 拉着 Nika 的手,紧紧攥着。逃离虚无是最痛苦的事。16 个小时里,她们在一栋拼尽全力要杀死她们的大楼里跌跌撞撞。
当 Nika 第一次吸入冷空气,寒气呛得她喉咙发紧时,她突然哭了起来。Lera 像根绷紧的神经,靠着顽固的意志和纯粹的巧合活了下来。她快撑不住了。可当她抱住 Nika 时,她知道自己愿意再来一次。
哪怕要跑一千次,哪怕会失败,只要能让 Nika 此刻在身边,她都愿意。
Nika 盯着长镜子里的自己。镜子靠在教堂的长椅上,她穿着新的格子裙,手顺着裙摆往下拂。城里的穷人和不幸的人在周围走动,分拣着教众捐赠的物品。
Lera 记得自己那么大时,也盯着过一条和 Nika 身上这条很像的裙子。那时还没有具体的想法,没有清晰的轮廓,只是模糊的渴望。Nika 穿这条裙子很完美,让她胸口某个地方安定了下来。在路人眼里,她们平平无奇,就像一对母女。
一个月前,这个想法还会让她僵住。在镜子里,她恐怕会看见列宁(Lenin)在南极。又是那种冻结死亡的意象,扯着她外套的下摆。
可没有。她转头时,看到的是 Nika 的手。Nika 神色复杂,在她和镜子之间来回看。
“我不是人。看起来像,但全是假的。” 她的声音很稳。Lera 皱眉,伸手搭上她的肩膀。除了母亲,她碰 Nika 的次数,比碰任何人都多。
“你不是人类,但这不影响你成为一个‘人’。” 她用尽全身力气说这句话,仿佛能逼 Nika 相信似的。话说出来却有些别扭,太生硬了,于是她又加了一句:“你可以选,每个人都可以选。”
“真的每个人都能选吗?你的样子是有原因的。我觉得孩子不该忘了自己从哪来。” 她语气那么肯定,让 Lera 心里一沉。
“这不是你应得不应得的事。每个人都能选。我就选了。” 说完这句话,Nika 终于从镜子前转过身。Lera 绷紧了神经,脑子里想着 Nika 对性别的理解可能是什么 —— 或许没什么概念,或许全是不好的。
Nika 眯起眼睛看着 Lera。她没打量 Lera 的胸口,也没看她裤子有没有鼓包。Lera 没有被审视,没有被拆解剖析。Nika 看透了她的身体,直抵她血淋淋的灵魂核心,然后笃定地点了点头。
“你选了。”Nika 笑了,Lera 也忍不住笑了。
当 Nika 放下盘子说 “我饱了” 时,Lera 差点哭出来。她强忍住,把那只一次性纸盘滑到自己腿上。
她们坐在长椅上,离海边还有 200 公里,可 Lera 已经尝到了唇上的咸味。
这是 Lera 吃过的最油腻、最可疑的街头小吃。卖给她们的老太太背驼得厉害,年纪很大了,却笑了。Nika 也回以灿烂的笑。
建筑师不该相信奇迹。在大学里,当她的国家重新定义自己,变得务实起来时,她学到了这一点。她学会了计算成本,学会了建造能容纳最多居民的公寓。务实,实用,坚固。
但圣彼得堡(St. Petersburg)有一座塔,400 米高,在那里弯着腰。






 血与肉与混凝土【幽灵工作室移植】
血与肉与混凝土【幽灵工作室移植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