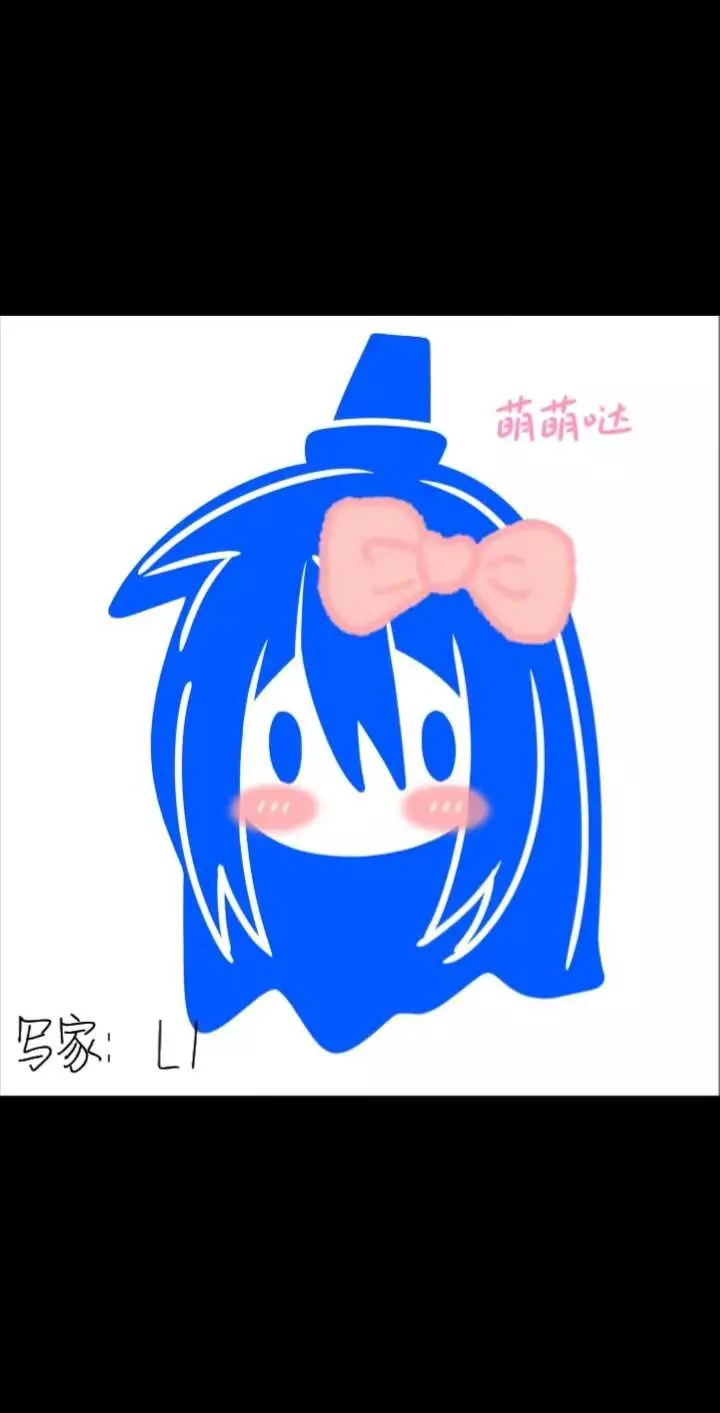《余.烬》自写小说😃
林砚第一次见到沈知年是在腊月的雪夜。他裹着洗得发白的旧围巾,站在孤儿院门口的槐树下,看沈知年被黑色轿车接走。那时沈知年穿着驼色大衣,指尖夹着半块没吃完的奶糖,朝他递来的动作带着迟疑,最终还是被管家轻声打断。
后来林砚靠奖学金念完大学,进了业内顶尖的律所,第一次独立对接的客户,正是沈知年。
沈知年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,指尖敲着桌面,目光扫过林砚简历时顿了顿:“林律师,我们好像见过。”
林砚握着笔的手紧了紧,面上依旧平静:“沈总贵人多忘事,我记不清了。”
他们的交集从工作蔓延到私下。沈知年会在加班后送林砚回家,会在他胃病犯时递上温水和药片,会在深夜的酒吧里,借着酒意说“林砚,我好像有点喜欢你”。林砚以为童年那点遗憾终于有了弥补的机会,却在签完沈氏集团并购案的那天,听到了沈知年和助理的对话。
“林砚那边不用再盯了,他手里的资源榨干了,留着没用。”沈知年的声音透过门缝传来,冷得像冬夜的雪,“当年孤儿院那点情分,不过是我看他可怜,随手丢的糖。”
林砚攥着合同的手指泛白,原来那些深夜的关心、温柔的眼神,全是精心编织的骗局。他没进去质问,只是默默转身,把那本写满沈知年名字的日记,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。
再后来林砚查出胃癌晚期,躺在医院里看窗外的雪。沈知年突然来探病,手里提着他以前爱吃的草莓蛋糕,语气带着从未有过的慌乱:“林砚,我错了,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?”
林砚笑了,咳着血摇了摇头:“沈知年,我不是你随手丢弃的糖,也不是你想捡就能捡回来的人。”他顿了顿,目光落在沈知年泛红的眼眶上,“当年那半块奶糖,我早就忘了味道了。”
弥留之际,林砚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,是小时候在孤儿院,他和沈知年的合影。照片里的沈知年笑得灿烂,他也跟着弯着嘴角。只是后来,有些人走着走着,就把心丢在了风雪里,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沈知年在林砚走后,才发现抽屉里的那份并购案补充协议——林砚把自己应得的所有分成,都捐给了当年的孤儿院,备注栏里写着:“给像我一样,曾渴望过温暖的孩子。”
窗外的雪还在下,沈知年抱着那份协议,蹲在地上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。可这一次,再也没有人会递给他一块奶糖,告诉他“别怕,有我呢”。






 233角色社区
233角色社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