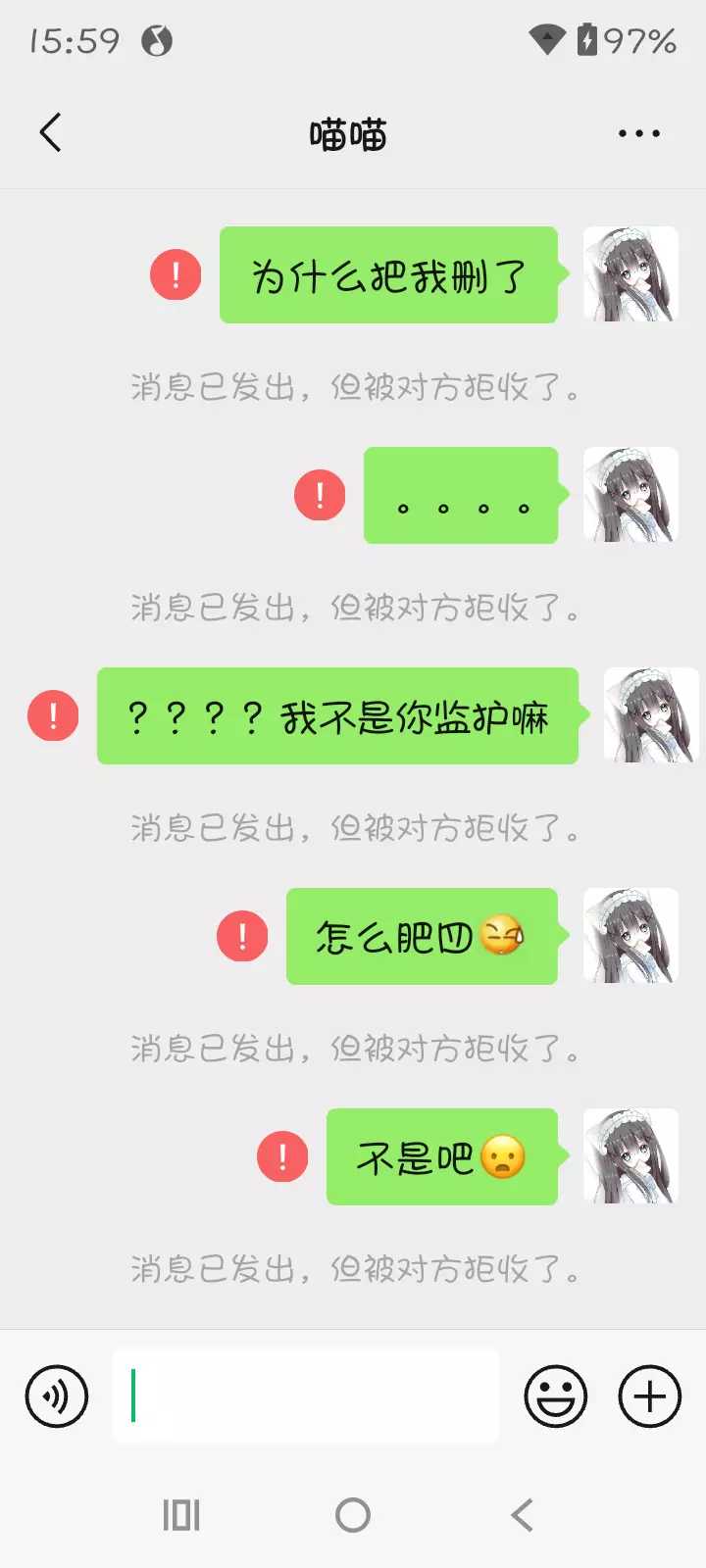《茶盏里的旧时光》
陈阿婆的竹椅在廊下吱呀作响,檐角的铜铃被风撞得叮咚。我蹲在青石板上,看她用布满老年斑的手指摩挲着那只青瓷茶盏——釉色温润如初春的湖,盏底还留着半圈茶渍,像朵开败的梅花。 “小满,过来。”她招招手,我便攥着衣角凑过去。阿婆把茶盏往我手里塞,掌心的温度透过粗陶传过来,烫得我一缩。“这是你阿爹的。”她忽然说,“那年他去茶山,说要给你挑个最润的盏。” 我盯着盏底的茶渍,那是阿爹的茶渍。他走的那年冬天,我趴在床头看他喝最后一盏茶,茶雾漫过他的眉眼,像层薄纱。“等我回来,给你泡桂花蜜茶。”他许诺的声音轻得像落在茶盏里的雪。 可他再没回来。 “阿婆,阿爹什么时候回来?”我仰头问。阿婆的手顿了顿,指腹擦过茶盏上的刻痕——那是阿爹用竹刀刻的“小满”,笔画歪歪扭扭,像他教我写字时总写不直的撇捺。“等开春,等山上的茶树抽新芽。”她把我的手裹进她皱巴巴的袖子里,“阿爹去给茶树赶虫了,等虫子赶完了,他就回来。” 我信了。 可开春后,茶树抽了新芽,阿爹没回来。清明雨落的时候,村里来了个戴斗笠的陌生人,说茶山塌了方,阿爹被埋在泥里了。阿婆当时正蹲在灶前煮茶,手里的茶壶“哐当”砸在地上,滚烫的水溅了她满手,她却像没知觉似的,盯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,嘴里反复念叨:“阿爹说等开春,等开春……” 那天之后,阿婆总在傍晚坐在廊下,捧着那只茶盏。茶盏空了,她就往里倒一盏凉水,然后对着盏底的茶渍发呆。我偷偷数过,她每天要倒七次水——像在等七次开春。 直到去年冬天,我在旧箱子里翻出阿爹的笔记本。泛黄的纸页上记着:“小满五岁,今日教她泡茶,她把茶包掉进水里,急得直哭。茶盏要温,心要暖,以后要给小满泡桂花蜜茶。” 我摸着纸页上的字,突然想起阿婆说“等开春”时,眼底的光。原来她不是在等阿爹,是在等那只茶盏里的茶再温一次,等“小满”两个字能被她念得不颤抖。 “阿婆,”我蹲在她身边,把茶盏捧到她手里,“我给你泡桂花蜜茶吧。” 阿婆的手抖了抖,茶盏在她掌心转了半圈。我往里倒热水,看水汽漫上来,模糊了她眼角的皱纹。“阿爹说,茶要慢慢喝,日子也要慢慢过。”她突然笑了,像多年前那个教我泡茶的午后,“小满,阿爹没骗你。” 风穿过廊下的竹帘,铜铃又响了。茶盏里的水开始冒泡,桂花香混着茶香漫出来,阿婆的手覆在我手背上,暖得像团火。 原来有些等待,从来不是等一个人回来。是等我们终于明白,那些没说出口的“等”,早就在岁月里生了根,长成了更坚韧的爱






 交友生活论坛
交友生活论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