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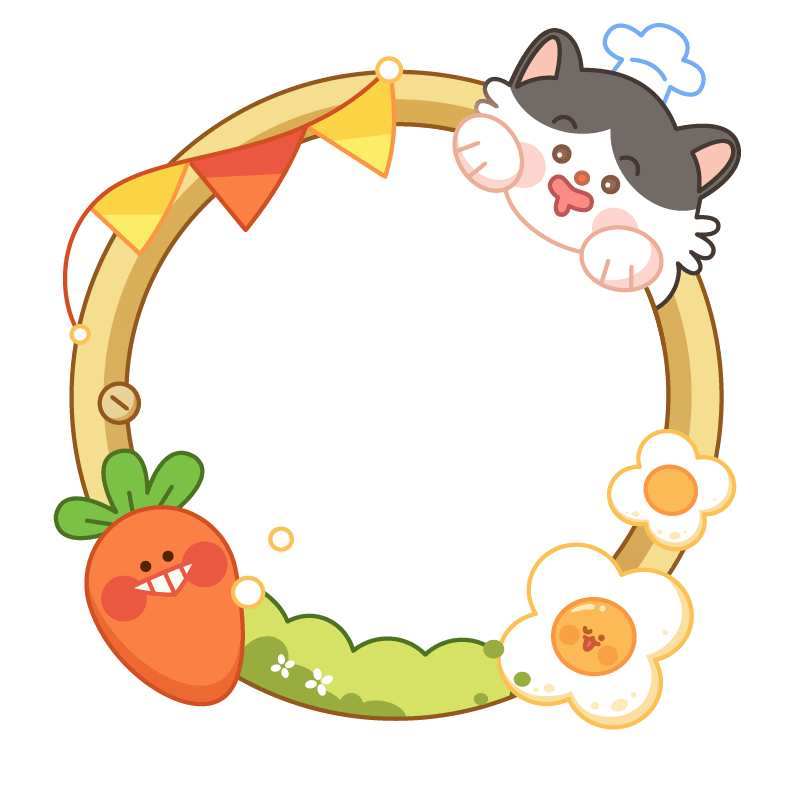
春秋蝉(已有闺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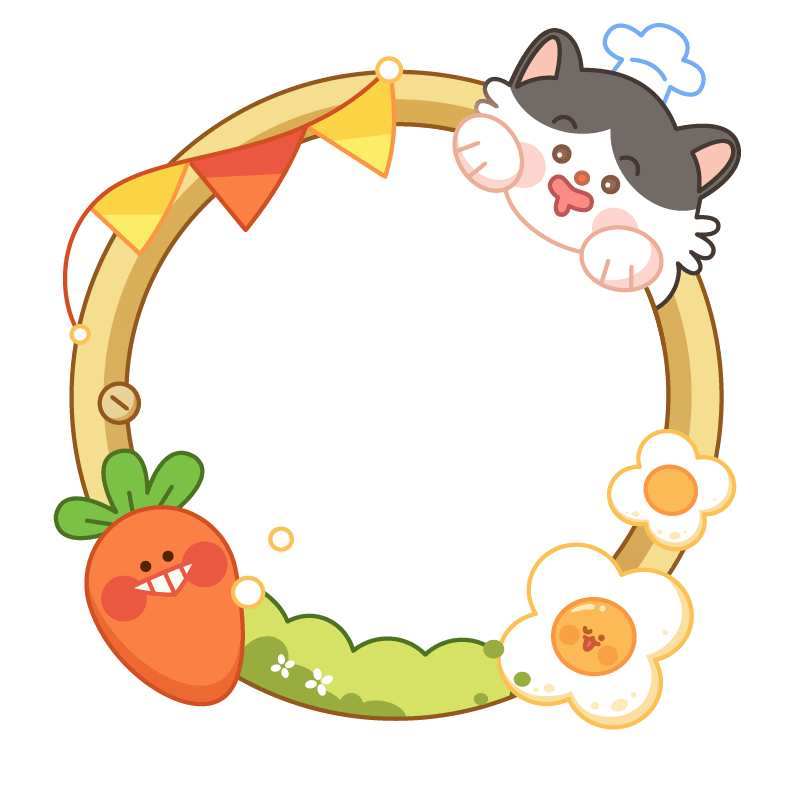
春秋蝉(已有闺)

233号:378915895广东
12关注
59粉丝
916获赞

闺蜜我独宠,她没钱我给她氪 ૮ ・ﻌ・ა
 看板娘-米米
看板娘-米米游戏档案
8
玩过游戏数量
298.6小时
总游戏时长
动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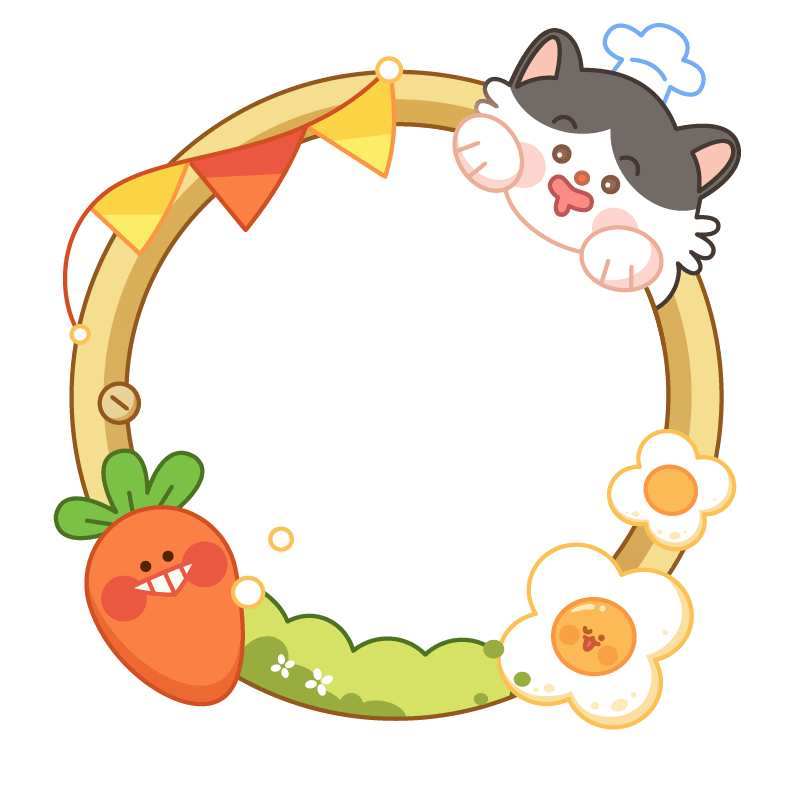
春秋蝉(已有闺)

简介
闺蜜我独宠,她没钱我给她氪 ૮ ・ﻌ・ა
 看板娘-米米
看板娘-米米12关注
59粉丝
916获赞
游戏档案
游戏总时长
298.6小时

玩过游戏数量
8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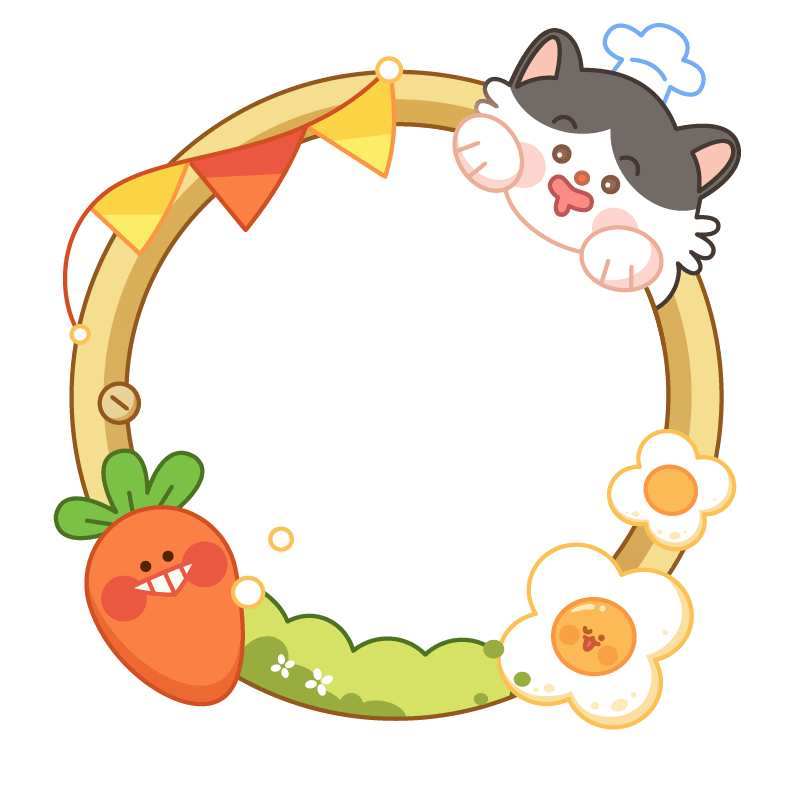
春秋蝉(已有闺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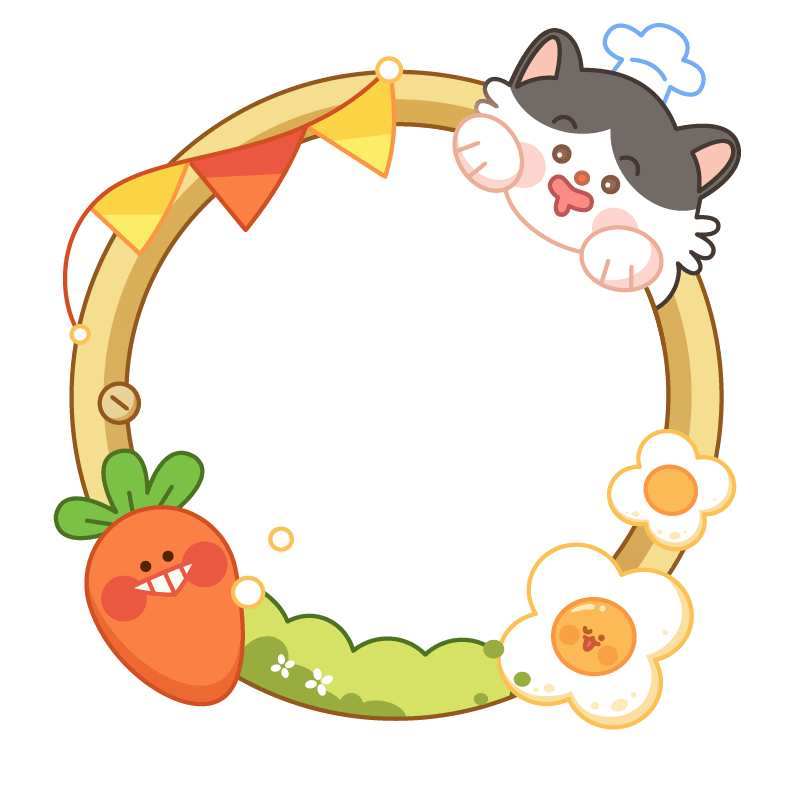
春秋蝉(已有闺)


闺蜜我独宠,她没钱我给她氪 ૮ ・ﻌ・ა
 看板娘-米米
看板娘-米米8
玩过游戏数量
298.6小时
总游戏时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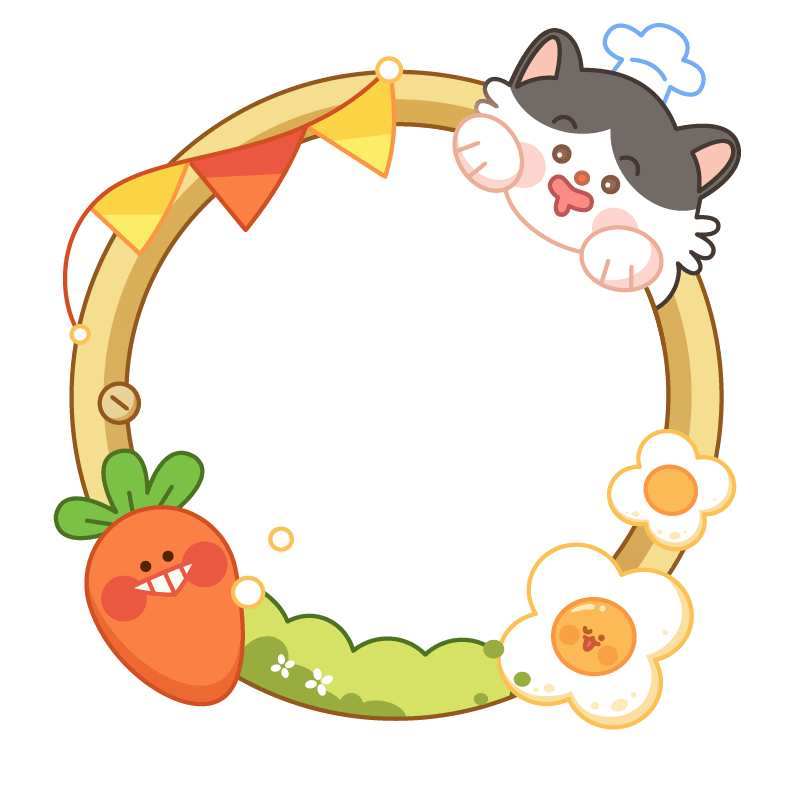
春秋蝉(已有闺)

简介
闺蜜我独宠,她没钱我给她氪 ૮ ・ﻌ・ა
 看板娘-米米
看板娘-米米游戏档案
游戏总时长
298.6小时

玩过游戏数量
8款
